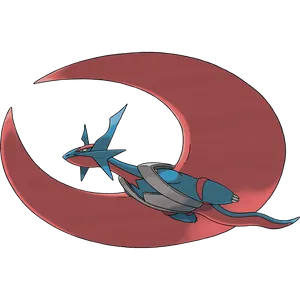生活和历史一样,都是由突变造就的
原创 作者:西坡 公号:西坡原创 发布时间:2023-08-07 11:41 发表于江苏
原文地址:生活和历史一样,都是由突变造就的
文|西坡
每个刚开始工作,练习掌握自己生活的青年人,都会计算,假如我今年挣多少钱,花多少钱,存多少钱,明年努力多挣一些,再过几年争取跳个槽、升个职、加个薪,那么在若干年后我的生活就会如何如何。
可是等到这个青年人到了中年,回头去看自己坎坷而平凡的奋斗史,就会发现生活的发展完全不是当时预料的样子。工作做着做着,可能一夜之间行业没了。在一个城市生活十多年,可能突然换个城市,从头再来。结婚、生孩子,从前的生活会彻底打乱重组。
生活不是线性的,中年人都懂得这个道理,而青年人普遍不懂。这是两个群体,不,是一个人在两个人生阶段最大的差异。
生活当然有线性的部分,但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努力把非线性的部分剪掉,让整个生命故事更加符合线性的外观。
老舍先生的《骆驼祥子》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祥子出场的时候,是一个励志青年,他对生活的理解就是线性的。
他年轻力壮,而且善于观察,进城不久就发现,拉车是更容易挣钱的活。他大概一算,只要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,“猛然一想,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,一百元就是一千天,一千天!”
祥子不仅骄傲于自己的身体,更骄傲于自己的精神,“不吃烟,不喝酒,不赌钱,没有任何嗜好”,他相信只要啃咬牙,事就能成。所以他对自己发誓,“他——祥子——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!”
可是事情一开始就出现了变故,他虽然拉上了包月,可是工作不稳定。而且他越是想着攒钱买车,拉车的时候就容易不专心,把车碰坏了要赔钱,买车的计划就要推后。老舍先生跳出来说,“不幸,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儿的。”
一直等了整整三年,祥子才凑足了一百块钱,终于弄了一辆车。但这时候,计划只是出现了微小的偏差,祥子对未来的想象依然是线性的。有了车之后,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了,“拉了半年,他的希望更大了:照这样下去,干上二年,至多二年,他就又可以买辆车,一辆,两辆……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!”
老舍先生又跳出来,“可是,希望多半落空,祥子的也非例外。”
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,不知道的可以去读小说,但最好不要像课本里教的那样,把它当成一部社会批判小说来读。你可以设想,假如祥子换一个时代,他的故事就不会重演吗?假如换一个国家,那里就没有祥子吗?再假如,换一个出身,让祥子含着金汤匙出生,他的生活就不会崩坏吗?想想含玉出生的那位哥儿吧。
祥子的悲剧,是永恒的悲剧。老舍先生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把它写小了,把祥子的失败总结为“个人主义的末路”。我们只要想想老舍先生自己的命运,就知道对个人主义的批评是多么站不住脚。认为集体主义更加有利于生活的线性发展,已被历史证明只是另一种妄想,或许是代价更惨痛的妄想。
《红楼梦》里的宿命论曾经被嫌弃“落后”“不科学”,但是相对叶圣陶、巴金、老舍那代小说家的世界观,却让我们觉得亲切、合理。这是历史给我们开的玩笑,意味深沉的玩笑。
更后来的陈忠实、莫言、贾平凹这些人,在讲故事的时候,又不约而同地回到了传统的宿命、因果、无可奈何。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光明的背面。我不认识这是一种思想倒退,它只是文学对历史的适应。
民国作家们,不管哪门哪派,大多数具有一种浅薄的进步主义思想,只是大家进步的方向不同,有人的方向是苏联,有人的方向是欧美。鲁迅是其中的另类,虽然他在社会观念上有倾向,但他对人生与世界在本质上的无序性,有超越时代的深刻认知。
我们幸好还有鲁迅。我们可以通过对鲁迅的解读,学习现代人面对无常的方法。
最能代表鲁迅思想的,不是犀利的杂文,而是暧昧的《野草》,鲁迅在《影的告别》这一篇里写道:
“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,我不愿去;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,我不愿去;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,我不愿去。
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。
朋友,我不想跟随你了,我不愿住。
我不愿意!
呜乎呜乎,我不愿意,我不如彷徨于无地。”
天堂、地狱、将来的黄金世界,“我”都不愿去,那么“我”要去哪儿呢?不知道,“我”宁愿彷徨于无地。“我”想要的,是自己的独立性,哪怕没有世界可去,也要获得自己的独立性。独立性大于一切。独立性就是主体性。
曹禧修在解读《影的告别》时说:影告别的对象不是神秘的上帝而是“人”,这就说明, 使人丧失自我的“形”原本就是人自身,是人的同类而不是人之外的任何他类。细言之,把人异化为影的“人”,可能是个人自身,也可能是个人自身之外的别的个人,抑或是以个人为单位所组构的群体。
鲁迅的意思应该是,人为了捍卫自己的主体性,应该敢于与一切世界为敌。世界就是体系,东方的体系、西方的体系,政治的体系、经济的体系,只要戕害了人的主体性,人就应该离开它们。“我独自远行,不但没有你,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。”这是多么巨大的勇气啊。
生活和历史一样,都是由突变造就的。我们和祥子一样,拼力守护着自己眼前可计算、可期盼的愿望,可是生活注定不会让我们如愿。风暴随时可能从任何一个方向袭来,有时甚至会从自己心底涌出。
但是鲁迅告诉我们,纵然我们失去了所有,我们依然可以拥有“我”。可是我们也可能在不知不觉间丧失“我”。所以不管是疾风暴雨还是风平浪静,我们都要反复练习一种技能,那就是在自己内部识别出可以代表“我”的部分,勿失勿忘。
继续阅读